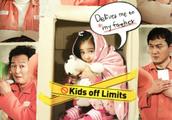熟悉《哈姆雷特》的讀者/影迷,當然會放心機在帕斯塔拿(Boris Pasternak)如何取捨的心思裡,看《哈姆雷特》(1964)視覺具體化的獨白時刻、關係情理、價值觀抵觸、互動的推進等,甚至,一些可能是哥辛薛夫(Grigori Kozintsev)、史莫敦洛斯基(Innokenti Smoktunovsky)的現場創作,如表達對白時的表情、神韻、小動作,也歸到這位《齊瓦哥醫生》(1965)作者的文本再安排的功勞上。

然而,這裡我要指出帕斯塔拿一個具爭議性的大膽剪裁,當國王克勞迪斯看了影射他殺兄的戲劇表演後,他再不能氣定神閒,回到密室對鏡煎熬:「我的王冠、我的野心,和我的王后,利益握在手,可以被寬恕嗎?」(I am still possessed of those effects for which I did the murder: my crown, mine own ambition, and my queen. May one be pardoned, and retain the offence?)居然對天懺悔起來。全片第一部份完結於此,哈姆雷特竟然不在場,他這個下手報父仇的機會,被帕斯塔拿「剝奪」去了。
這理應是一個神學的問題。莎士比亞要哈姆雷特潛行在場,其實是一種心性考驗。心思細密、極聰明的他想到,若然他在懺悔時下手,會讓克勞迪斯得到上天的原諒,有可能上天堂,他在世間的罪行會一筆勾銷,他實在不能這樣便宜這個殺父佔母的仇人,讓他「好死」。
縱使來自新教家庭,莎士比亞卻知道英國從前根深蒂固,有天堂有地獄,也有煉獄的觀念,縱使不是但丁的三界旅程,哈姆雷特的困惑,也盡然是人在天地間存疑反反覆覆的思慮;他不想克勞迪斯上天堂,他懷疑父王不得好死,不能到煉獄去,要滯留人間,他質問天庭,他自己是否也正身在人間地獄,「這片大地,負載萬物之靈的美好框架,彷彿只是一個不毛的荒岬」(That this goodly frame, the earth, seems to me a sterile promontory)。
哥辛薛夫與帕斯塔拿讓哈姆雷特在克勞迪斯對鏡低泣跪下時消失,對於深思世故的莎士比亞讀者,自然未必滿足於以社會主義唯物論的主調來配合這個說法,而是繼續去看這部說俄語的《哈姆雷特》,在文本取捨上呈現了怎樣異於莎士比亞的另一個人間煉獄。哈姆雷特的「不在場」並非單一存在的刻意技術性選擇,而是一個標誌性提點,令我們盡快進入討論狀態,去探究哥辛薛夫與帕斯塔拿完整的改動概念。